China's abortion regime
And the heroes fighting it—a street-level look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ummer we publish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ories a WORLD reporter has ever produced. Some writers have given us the view of China’s abortion regime from 35,000 feet, but June Cheng went into a dingy abortion facility in southwest China and saw where the operations are performed. She met and wrote about compassionate men and women who are growing an indigenous Chinese pro-life movement.
Americans have concentrated on the evil of China’s official one-child policy, but June’s articl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issue is not just people vs. government. “If only it were all so simple!” wrote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f only there were evil people somewhere insidiously committing evil deeds, and it were necessary only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rest of us and destroy them. But the line dividing good and evil cuts through the heart of every human being.” Similarly, the front line of the battle to save babies’ lives runs through every heart.
That’s why it’s vital for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emselves to learn what’s happening in their country. We’ve translated our July 26 cover story “China beachhead” into Chinese and have posted it below.
WORLD believes this article is of such importance we’re making it available to nonmembers of WORLD News Group. Please share it via email and social media (see sharing options in the blue bar above) with Chinese church pastors, Chinese Christian ministries, missionar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o work with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ny others who can benefit from reading June’s report in their own language. —Marvin Olasky
中国抢滩
处于堕胎手术实施最多的国家,中国反对堕胎组织的努力正在成长中。但拯救尚在子宫内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在教会内部也一样。 —程君
中国—米饭和炒牛肉的气味飘入中国北方一所由简易仓库改造而成的教堂. 通情达理的主人向来访者手中递上热开水—这种无论天气如何都是最佳选择的饮品,安装在墙壁上的风扇将空气带入温暖的房间。在两位牧师—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中国人—结束了“神圣的生命”课程教导后,各个年龄的男男女女们站了起来,抽泣、祷告、忏悔:“主啊,原谅我放弃了我的孩子,我不知道这是谋杀,神啊,请原谅我流无辜人的血。”
对于房间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发育中的胎儿的照片,了解堕胎所带来的后果,并研读圣经中对神圣的生命的教导。一个短发的中年中国女子带着紧张的微笑走近我。 “那些被流产掉的胎儿哪儿去了?”她问,眼中含着泪。 “我以前堕过胎,我想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我用蹩脚的中国轻声地说孩子们去天堂,告诉她大卫王的孩子的故事。 “哦,听到这样的消息真好,”她说。
在中国,曾经有一名女士告诉我堕胎“就像喝水一样”,据官方统计每年有130万婴儿因堕胎手术而失去生命,迄今这数目为全球最高。对于许多人来说,堕胎被认为是控制生育的首选方法,在巴士和广告牌上充斥着快捷、价格便宜、无痛人流手术无处不在的广告。出于政府继续人口控制政策的事实,很少有人,包括基督徒,了解子宫内的生命或是人工流产过程。然而,不只是一胎化政策导致女性采取堕胎手术;年轻一代对于性关系松懈的态度与传统看法中非婚生子所带来的耻辱产生的冲突,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采取堕胎手术。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基督徒开始对生命表明立场,既在教会的讲坛上以圣经的教导来谈论堕胎,同时也帮助女性以,通常是,非传统的方式来保护生命。有些人最初是通过来自美国的福音事工听到维护生命组织,有的通过互联网或海外的教导,而另一些则通过阅读圣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通过那些渠道,这个信息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教会,也使母亲们怀中抱着咯咯笑的婴儿保存了性命,女性免于被迫堕胎,教会因为悔改以及帮助自己而不断成长壮大。可是根据维护生命组织,中国生命协会(CLA)的调查,在中国所有的教会中只有大约1%的会众听过圣经中关于生命的教导。由于文化,政府,和实际性的障碍阻碍了他们的信息,中国的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早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昏暗的非法医疗诊所里,似乎连光线都无法穿透。在一个铺着薄薄一层床单、散发着霉味的单人床和立着一个静脉滴注瓶架子的房间旁边,一个粗壮的女医生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向我吹嘘她给女性们实施堕胎手术的经历,她做人工堕胎手术已经40年了,现在同时在医院和诊所里工作,(诊所里能赚到更多的钱),她保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手术—有一个女孩已经堕胎8次了,而且现在过得很好。
虽然中国的法律禁止孕晚期人工堕胎,她说不管预产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她都能实施堕胎术,“即使(婴儿)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哭了” 。孕期三个月内的堕胎术花费仅仅一千人民币(160美元),患者进出诊所的时间一共只需两小时。她接着带我参观实施堕胎术的地方,一间上了锁的、充满了化学品和死亡臭气的房间。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带脚蹬的手术椅,那个医生快步走过去将上面从前一个手术留下的血迹斑斑的卫生纸揭下来,她的前一名手术患者是一名怀孕5个月的18岁女孩。在单人床和桌子中间夹着一个非法的超声波仪器,上面盖着一块布,这是实施堕胎手术的人用来提供鉴别胎儿性别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在中国是非法的,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已扭曲了国家的性别比例。
然而,距诊所大约一个街区之遥,矗立着一座警察局,公然无视街上的非法行为。创立中国生命协会的美国宣教士马克·李表示,警方暗中赞同这些诊所,因为他们降低了该国堕胎的官方数字。尽管依政府计算每年有130万例堕胎,但包括那些没有报告的堕胎术的实际数目可能高达300万例。
在中国,学校里不进行性教育,因为老师们不好意思去讨论这个话题,家长也不跟孩子谈性,于是孩子们就从媒体中学习,包括性行为露骨的西方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其结果是,超过70%的中国人有婚前性行为,与20年前相比增长了30%。
对于怀孕的未婚少女,人工堕胎往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未婚妈妈为家庭带来耻辱,于是家长向他们的女儿施加压力去堕胎。如果一名女性保住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支持她的系统,就可能会失去她的工作,被学校开除,并且在将来很难结婚。此外,孩子将无法获得允许去上学、旅行、或是找工作的户口或户籍。让别人领养孩子也很困难,因为政府限制私人领养,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法定领养程序。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住进医院或非法诊所,花两个小时和1000人民币,然后返回到正常的生活。已婚夫妇在一胎化政策下通常认为堕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虽然在一些地区执行法律时已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譬如说少数民族和独生子女家长具有豁免权—生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往往被迫支付罚款,罚金为他们所居住城市的税后人均收入的3至10倍。对于那些在属于政府管理的工作场所工作的人来说,有第二个孩子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因为这种行为为社会设立了一个坏榜样。虽然政府正式禁止强制堕胎,这种行为依然继续在农村、当地官员不懂法律的地区发生。
特别是即使自从中国在1979年开放以来,教会已经成倍增长,但教会对于人工堕胎这一话题一直保持沉默。前家庭教会牧师王彼得*现在花时间培训像之前所提到过的那个中国北方教会那样的教会,他说自己遇到过一些自己曾经堕过胎或者提供教会会众经济帮助,以支付她们人工堕胎的费用的牧师。有些牧师,特别是农村地区,从来没有接受过堕胎是错误的或者为什么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教导,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话题过于敏感,不希望让政府再有迫害他们的教会的借口。
但最近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认为中国有必要进行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麦克. 李于2010年创建了中国生命协会,开始了分散式网络的教会和福音事工,都是以分享维护生命的信息并帮助妇女保住她们的孩子为目标。通过将经验丰富的美国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的资源与中国教会的领袖相联系,中国生命协会能够装备当地的信徒很快开始他们自己的事工。该组织已经设立了孕妇安全庇护所,堕胎手术救援队,基督徒法律援助事工,一个中文的资源网站,和一座怀孕求助中心。李说,到目前为止,约有2万个教会听到了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的信息,而每一个听到过这个信息的教会每年能挽救2到5个孩子。
提供给母亲们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的解决方案需要改变以应对中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生命协会中,实际的工作是由当地基督徒们着手进行,像是黄撒拉,一位30多岁、性情开朗、表达特别,譬如说“热得我要吐血了”一类的家庭教会牧师。在2012年黄牧师差点把她的儿子人工流产掉,她看到了保护生命的重要性,并开始为中国生命协会工作,从那时起,她开始了仅有她自己一个人的福音事工,并已经挽救了50到60个孩子的生命。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下午,黄牧师的两部手机不停地响,都是母亲们寻求她的帮助:“我该拿我的第二个孩子怎么办?”“我怀孕了,我没有钱照顾这个孩子。”“政府官员强迫我做人工流产,你能帮忙吗?” 打来的电话中大多数是针对一胎化政策的问题,黄牧师果断地以挑战教会帮助家庭支付罚款,为孕妇找到安全的住所,以保持孕妇远离亲人的压力,或威胁要上报继续实行强迫堕胎的计划生育官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火烧眉毛的问题。对于那些仍然无法支付高昂的罚款的人来说,可以将孩子生下来,然后在黑市以罚款金额的一小部分来为孩子买户口。黄似乎一分钟都不闲着,她每周去农村进行性教育,然后去堕胎诊所和医院与年轻女性交谈,说服她们摆脱堕胎的想法。每次至少有一位或两位女孩最终会记下她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她甚至与前面所提到过的堕胎实施者建立了关系。
尽管挽救了生命,黄发现很难得到当地教会的支持:支付不起自己的牧师的教会没有钱支持其他的需要。中国生命协会也面临着其他的试炼: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官员逮捕了几个与中国生命协会有关联的同工,并告诉他们该组织正在被调查中。警察阻扰了一次预计于三月份举行的全国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的会议,但牧师仍然在不同的地方见面,为教会中的人工堕胎而祈祷和忏悔。
吉姆·彼得斯,一位资深的美国维护生命、反对堕胎运动积极分子,也把他的注意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这里,他于2010年亲眼目睹了教会是何等急切地需要听到圣经对堕胎的教导。以他的教牧身份,他提出一些圣经章节,像路加福音第1章,当施洗约翰在以利沙伯的腹中欢喜跳跃,马利亚刚刚怀了即将到来的耶稣—来证明圣经对生命始于何时的教导。彼得斯穿梭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聘请了王某全职服事在全国培训教会领袖。
即使是牧师们起初很犹豫不决听这样的信息,一旦王某开始讲道,“他们的眼睛睁大,如果我讲一个小时,他们会听,如果我讲四个小时,他们也会听。 ” 他甚至能在国家承认的、挤满了700到800名听众的三自教会中讲道。
通常在教导之后,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吴路得,一个天真活泼的年轻女子,记得自己在一所教会中时遇到王在讲道,内容是针对圣经中对人工堕胎的教导,她感到自己有罪。过了几天,她发现自己怀了前男友的孩子。
“在我的心中,我的想法是顺服神, 但是现实上似乎是我不能留下(孩子),因为我的父母是不会理解和支持的。” 于是,她三次去医院做人工堕胎,但每次她最终都走了出来。她向王寻求帮助,他通过他的教会,为她找到一份工作以及住处。在她的整个孕期中—她向她的家人保守了这个秘密—教会成员给她带来了食物,还来看她,在产房里陪护在她的身边。一旦她的女儿出生后,教会中一对老夫妇私下将她带回他们的家中照顾。
几个月之后,吴小姐与她的读经的带领者结婚,两人并且加入了All Girls Allowed (接受所有女孩),一个美国非营利的组织,希望能够帮助其他跟她曾经有一样经历的年轻女性们。 AGA是由前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柴玲所建立的,该组织提供面临选择人工堕胎手术的女人经济上的帮助,也因此提供和这些家庭分享福音的机会。
在王分享信息的另一个教会中,教会里的会众告诉他,附近的一个医院有一个负责人是基督徒,还有几个护士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尝试在医院內开一个怀孕中心呢?医院负责人同意了,并要求每一个来堕胎的女性进来后先在一个粉红色和黄色的房间与一个志愿者辅导员交谈。起初,有大约20名来自彼得斯和其他美国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组织的积极分子的志愿者参与了初级卫生保健培训,而当该中心2013年5月开业时,志愿者的人数下降到了10人。
志愿者玛丽陈*说,在该中心开业的那一年里,挽救了5个孩子的生命,她给我看了她手机中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个捆在小毛毯里、胖乎乎的婴儿。大部分的婴儿都是单亲母亲所生,而那些母亲们现在都与她们的男友结婚了。但是三月份开始出现了困难,医院安排了一个医生负责该中心,但他不允许辅导员与患者见面。志愿者被转为与刚刚做完堕胎术的女性电话联系,进行跟进辅导。但更大的问题是,即使辅导员可以与患者见面,也不会有足够的人来协助中心的工作。由于繁忙的工作日程以及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分歧,志愿者人数已减少到三人。陈姊妹想知道中心是否能找到一种方法来聘请受薪职员。她说,她知道在医院中设立一个挽救生命的中心是神所命定的,只能祷告祈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各地迅速扩展的庞大家庭教会互联网中,家庭教会领袖们正在兴起,不依赖任何海外福音事工组织。在成都,一个由500名教会成员组成的秋雨之福教会中27岁的范弟兄于2012年在博客上看到一组人工堕胎的图片,对国内的高堕胎率而感到内心受到谴责。因此,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和他的教会同工们一直在印刷福音小册子和单张,要求母亲们不要在6月1日采取人工堕胎术,因为这一天是儿童节。范弟兄以自己的营销经验设计了精美的小册子,解释在中国人工堕胎的方式、在福音中找到的盼望以及联系他的教会的方式。去年,他扩大了他的事工,包括在公交车上做广告宣传,当局以未经批准印刷宣传材料为由逮捕了他和其他几个同工。今年,范弟兄印刷了50000份单张,由他的教会向社会分发,一个教会同工因为分发单张而被警察殴打。
在秋雨之福教会中,保护生命的要点显明在教会服事中带着两个孩子的会众家庭中。范弟兄说,大多数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没有户口,他们对将来要怎么办不得而知。除了买户口的办法以外,这些家庭也可以等到全国人口普查,那时候工作人员有时会免费为孩子们登记,好让自己的工作轻松一些。有一个好处是,秋雨之福教会拥有自己的私立基督教学校和神学院,因此没有户口也不能阻止他们接受教育。
在一年中的剩余时间,范弟兄带领一个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组织的小组,这个小组的事工专注于教导教会成员们反对人工堕胎,并已经扩展到收养和照顾孩子的服事。去年,一个教会成员在医院外面分发单张,劝说一名年轻女性留下自己的胎儿,范弟兄为她联系到一个愿意私下收养这个孩子的家庭,并意识到这将是他的事工中下一个很大的需要。
他的6月1日活动激发了其他同工利用这一天谈论反对人工堕胎的想法:今年彼得斯和王弟兄开始了长达一个月、于6月1日结束的活动,培训教会领袖在教会互联网传播有关反对人工堕胎的教导。据王弟兄说,最后有大约8200名牧师在他们的教会中教导反对人工堕胎。范弟兄说,有人向他询问有关反对人工堕胎的工作,对此他不是一个专家,他只是一个出于自己的信念而对此有所作为的基督徒。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的堕胎率增长过快; 这太可怕了,”范弟兄说:“我相信:我们不能杀人。但中国人都犯了这样的罪。我不想让下一代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程君是一名作家。来自中国的报道
出于保护,文中使用了化名
An actual newsletter worth subscribing to instead of just a collection of links. —Adam
Sign up to receive The Sift email newsletter each weekday morning for the latest headlines from WORLD’s breaking news t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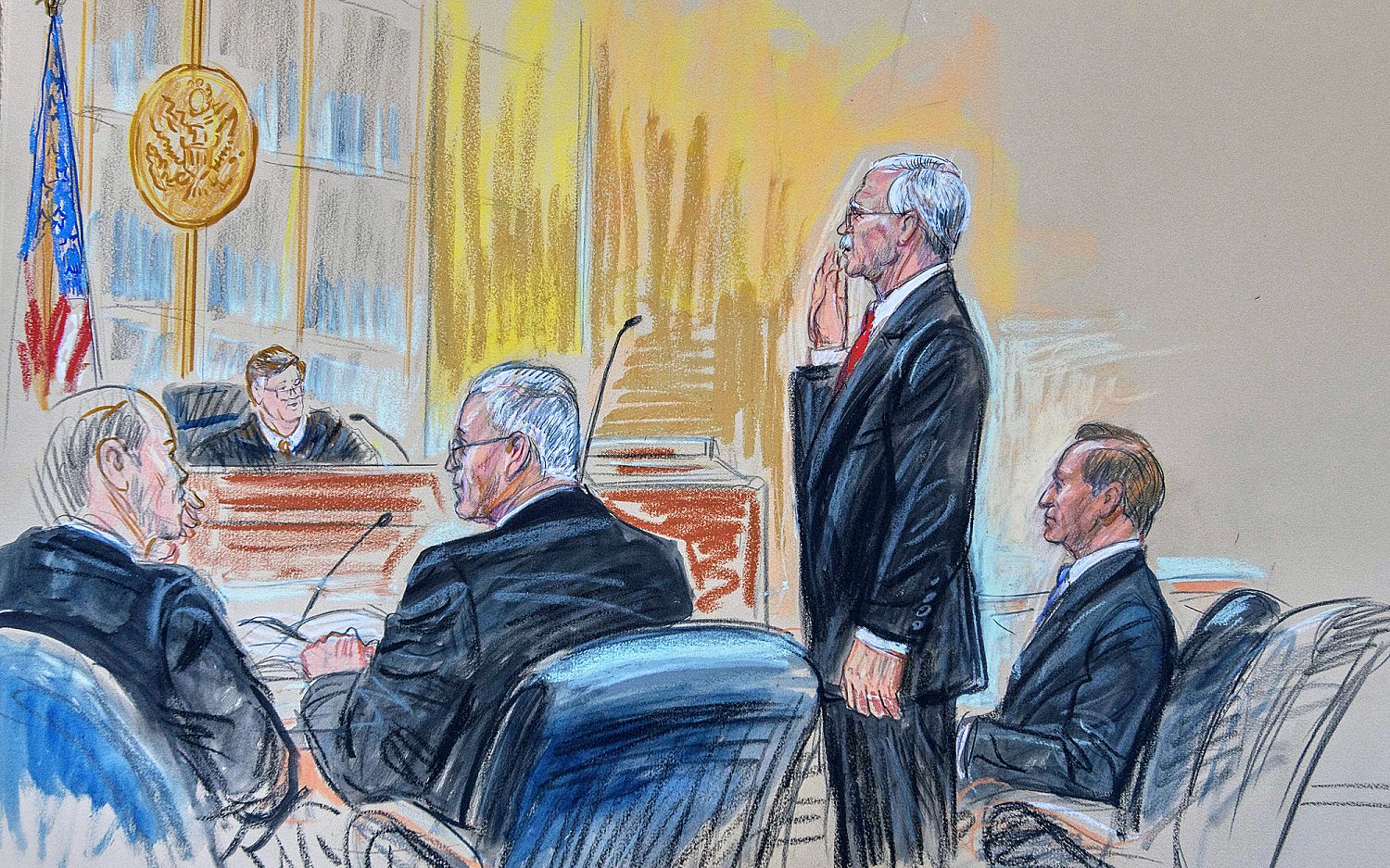


Please wait while we load the latest comments...
Comments
Please register, subscribe, or log in to comment on this article.